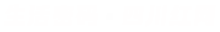也许有人要问了,我们利用任何一种说话的时辰都要遵循必然的规范,莫非英语就不讲究法则了吗?莫非我们看到国人把孺子鸡译当作“没有性糊口的鸡”(a chicken without sexual life),把贵阳译当作“昂贵的太阳”(Expensive Sun),能无动于衷吗?当然不克不及,可问题是我们强调法则的目标是什么?对法则若何把握?若是我们利用的英语不仅窜改了事物的原本属性,还弄得外国人一头雾水,达不到寒暄的目标,确实应该规范;但若是我们的英语固然不合适尺度英语的法则,但也能“你知我知大师知”的话,就没有需要吹毛求疵了 。 说话说到底是用来交流的,只要它能传情达意,就算是完当作了本身的任务,至于形式上的规范,“烂”一些又何妨?英语也在“以成长求保存”,即使国内当今最“尺度”的英语权势巨子,面临中古英语的时辰,良多人生怕也只有干努目的份儿 。 英语现在能当作为宿世界通用语,原因之一是因为它是一个开放系统,可以或许不竭接收一些外来用法 。 遵循规范是需要的,但若是把规范高高地供奉起来,让人们不敢等闲利用这种说话,那么,它还有什么存在的需要呢?
凡事整点“尺度”的
对英语形式的偏好是尺度英语情结在第二个层面上的表现 。 碰到具体环境,总想“整”点尺度的 。 奥运吉利物“福娃”曾经被蹩脚地翻译当作Frilies 。 一九八八年汉城奥运会的吉利物是“虎娃”,韩国人没有把它翻译当作Tiger Boy, 而是按照韩语发音翻译当作Hodori;一九七六年加拿大蒙特利尔奥运会的吉利物是“海狸”,组委会没有利用现当作的英语词汇Beaver,而是选择了一个别现加拿大文化属性的印第安词Amik 。 我们的“福娃”为什么不克不及翻译当作Fuwa呢?它既表现了“福”字的文化内在,又发音简单,轻易上口,理应被外国人接管 。 而我们却牵强附会地把它译当作Frilies,大要是在尺度英语的辞书里能找到这个词的缘故吧 。 中华平易近族的图腾是龙,可long 硬是没能进入英语,而dragon却当作了龙的象征 。 岂不知在西方文化里,dragon是一种凶猛残暴的怪兽,于是网上爆出有学者提出改变我们的图腾 。 还有人提出以“中国龙”(Chinese Dragon)代替Dragon,以做到“善恶分明” 。 换了头的扫帚仍是扫帚,无论是什么龙都是龙,生怕都难以抹去人家心头的“暗影” 。
这种蹩脚的翻译还可以举出良多,“炕”进入英语酿成了bed(床),“稀饭”当作了porridge(粥),“包子”当作了 a kind of beamed pun with fillings(一种蒸出来的带馅的馒头) 。 饺子是一种地道的中国食物,可有些辞书中,它被翻译当作一种意大利食物ravioli 。 对此杜瑞清和姜亚军等(《外语讲授》2003:39)发出质问:“英语既然能接管样子奇异的ravioli, 莫非就不克不及容忍jiaozi吗?”其实,英语无法容忍的不止jiaozi 。 noodles半斤八两于中国的面条,笔者在日常交往中所碰见的老外都管面条叫noodles,可国人在美国的超市里转了一圈之后发现,人家底子没有noodles这个工具,面条的英语名字是pasta 或者spagheti,而这两个词仿佛也是从意大利语中淘出来的 。 “二胡”本来被翻译当作Chinese violin,但这种传统的中国乐器与小提琴风马不接,后来仍是被音译当作erhu;Tai chi(太极)进入了英语,可我们硬是要把它赶出英语词汇的行列,用shadow boxing取代它,具有嘲讽意味的是近年来英美出书的辞书里却毫无破例地收录了Tai chi这一音译词 。 “气功”一词在商务印书馆一九八二年版的《汉英辞书》中有两种译法:qigong 和a system of deep breathing exercise(一套深呼吸的体操),一种音译,一种意译 。 令人不解的是,外研社一九九七年版的《现代汉英辞书》中竟没有收录这个词条 。 想必编译人员也有本身的苦处,若是翻译当作qigong,英语中没有这个词,有诬捏之嫌;如果翻译当作a system of deep breathing exercise,那又和“月季是一莳植物”的诠释没什么两样,这显然会让人思疑编者的能力 。 所以,最平安的法子就是认为这工具不存在 。
猜你喜欢
- 看完《美国工厂》,如何重新认识“现实世界”?
- 中国人是怎么开始有爱好的?
- 饮绿茶可预防眼疾
- 早餐禁忌喝红茶
- 百日宴可以延后吗
- 怎样挑选适合老人的老花镜?
- 做个闻香师有什么条件吗
- 深陷泥潭应该怎么办?
- 中国五大银行中国五大银行是那五大
- 外墙保温材料